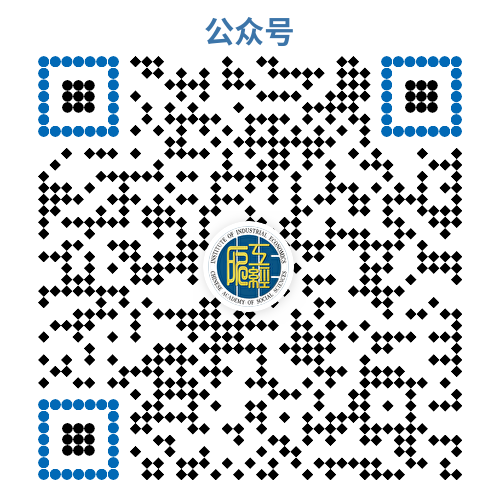|
摘要:新型电力系统是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改变了电力系统结构、技术、网络、供应链等形态,在提升国家能源体系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系统运行、网络安全、供应链等方面的安全风险,经济成本高、效率低等经济风险,以及碳减排技术不成熟等低碳转型风险。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进程,在“立”与“破”的协调推进中实现电力高水平安全,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有效有序推进电力系统“两化”转型发展,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培育形成能源新质生产力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能源体系;能源新质生产力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煤炭战略功能定位与测算”(编号:23BGL014)。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作为我国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重要内容。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当前乃至“十五五”时期的重点发展任务。自2021年中央财经委第九次会议提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以来,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也面临着一些安全风险和问题。2023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要科学合理设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路径,有计划分步骤逐步实现新能源的安全可靠替代。因此,需要系统分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对电力系统结构、技术、网络、供应链等形态的影响以及为国家能源安全带来的风险与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范,持续提升国家能源电力安全保障能力,为“双碳”目标实现、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进展
“十四五”期间,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政策体系逐渐完善,电力结构更加清洁低碳,技术路线和输配网络更加多元化,供应链更加系统化和灵活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朝着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柔性灵活、智慧融合的方向发展。
(一)政策体系逐渐完善
自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来,国家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推动出台法律法规、配套政策、实施方案等,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渐完善。“十四五”初期,国家新型电力系统的政策体系主要集中于新型储能发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能源行业标准计划、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能源高质量发展、能源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国家编制了现代能源体系和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十四五”中期,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了《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同时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政策《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指导意见》出台,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指明了方向。“十四五”后期,配套性政策、法律法规、实施方案都相继出台,如在电力安全治理、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发展、新型并网主体涉网安全能力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国家制定、出台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编制和印发了《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政策体系持续丰富完善,有力推动电力系统建设稳步前行。
(二)电力结构更加清洁低碳
电力生产消费结构朝着更加清洁低碳的方向调整。在电力生产方面,2021年,我国火电发电量占比仍高达71.13%,其中煤电发电量占比6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为34.6%,煤电装机占比46.7%,以风电、光伏等为主的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超过45%,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新增总容量的比重为78.3%;2023年,火电发电量占比已降至69.95%,煤电装机占比已降至39.9%,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已提高至53.9%,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新增总容量的比例已提高至83.0%。在电力消费方面,绿色电力消费和交易持续增长,电能替代有序推进。2023年,绿色电力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已提高至17.7%,核发绿证和绿电交易累计电量分别为1.76亿个、611亿千瓦时,是2022年的7.8、10.5倍。2023年累计完成替代电量734.37亿千瓦时,其中工农业生产制造领域的电能替代占比为46%。
(三)技术路线和输配网络更加多元化
随着光伏发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电力系统技术路线开始由大规模集中发电向大规模集中发电和分布式发电并行发展,即新能源发电除了采取大基地的大规模集中发电模式,还采取屋顶发电、墙体发电等分布式发电以及分散式风电等模式。电网结构也发生了转变,电力输配网络由传统的集中式大电网模式逐渐向大电网、地方电网、微电网并行模式发展。在传统的大电网模式下,输配网络是纵向一体化的集中式电网,且呈现出输网强、配网弱的结构。随着高比例新能源和高比例电子设备广泛接入电网,以及大量分布式光伏、小型新能源电站、微电网等出现,电力输配网络从传统的稳定电网向高弹性电网有序发展。通过电网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建设电力物联网,实现智能化调度、主动防御,调度模式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向“源网荷储”全网协同转变,推动输配网络向分布式扁平电网转变。
(四)供应链更加系统化和灵活化
随着电力低碳发展,电力供应链发输配售用各环节更加多样化,电力供应链整体呈现出由单一向系统化、灵活化转变。即电源侧由煤炭、煤电机组等火电供应链向火电、水电、核电、光伏发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地热发电等多种类型发电供应链系统转变;输电侧由传统高压线路与传统传感器向特高压、超高压线路、分布式线路与智能传感器转变;配电侧由传统配电变压器等设备和设施供应向智能化开关设备、变压设备、融合终端、故障指示器等高比例电气设备转变;售电侧由传统的电表、售卖电向智能化交易平台、智能电表等转变;负荷侧由传统的负荷中心、单一电力供应向源荷一体化、综合能源供应发展转变。生产侧多能互补的趋势更加明显,电力网络与通信网络融合发展成为主要方向,消费侧电冷热气水综合能源供应的需求不断增多,推动更多分布式综合能源服务商等新型主体进入供应链,在提升供应链灵活性的同时,也使电力供应链成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
二、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会使电力系统形态特征发生变化,给国家能源体系带来系统运行、网络安全、供应链等安全风险,经济成本高、效率低等经济风险,碳减排技术不成熟等低碳转型风险。
(一)电力系统运行、网络安全、供应链等面临的风险增加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会使电源结构、电网结构、调度方式以及源荷作用机制均向复杂化方向转变,使得电力生产、传输、分配和消费各环节以及整个电力系统面临的运行风险大幅攀升。现阶段,建设中的新型电力系统呈现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和电力电子设备、低系统惯性和抗干扰性、早晚和冬夏为高峰等特征,这些特征使次/超同步振荡风险增高,调频能力下滑,无功支撑不足使得电压不稳定风险增高,耦合关系复杂使得功角不稳定风险升高。风电和光伏发电不能“源随荷动”,且其出力容易受季节和极端天气影响而不稳定,这导致电力供应难以达成平衡状态。电力系统转动惯量、频率等重要参数的不稳定问题容易造成新能源脱网或出现电力系统故障。受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的出现愈加频繁且剧烈,进而放大新能源波动性、间歇性特征,使得保持电力实时平衡的难度进一步增大,导致电力系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的韧性和安全水平降低。同时,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以及源网荷储互动融合的增强,数字技术在电网的应用使电力系统面临与日俱增的网络威胁。并网设备的快速增长,更是扩大了潜在的网络攻击面。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推进,电力系统供应链节点企业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一次能源企业中的新能源企业增多,碳交易中心、设备供应商、电力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电力调度中心、电力交易中心等主体均成为节点企业,使得电力系统内部风险更加复杂。能源转型风险和宏观环境风险等电力系统供应链外部安全风险增加,如能源低碳转型带来电价加速上涨风险,在平衡煤电退役成本与新能源投资建设成本方面具有较高难度,经济成本较高;电化学储能技术、氢能技术等技术创新及集成应用仍不成熟,存在不确定风险。
(二)电力市场机制不完善易导致经济成本高、系统效率低
尽管电力市场建设的体制框架已基本建立,但诸多机制问题仍制约着其发展,难以契合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现实发展需求,成本与价值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畅通传导,经济成本高、系统效率低的问题仍普遍存在。一是电价的成本疏导机制仍不完善。市场与政府调控的机制冲突问题,导致辅助服务定价不合理,容量电价执行不到位,不能形成与电源功能特性相匹配的电价,也不能形成体现价值和供求关系的用户成本分摊机制。二是新能源电力参与市场交易的机制仍不健全。新能源入市参与交易的机制欠缺,参与市场电价水平偏低,辅助服务补偿机制不合理,灵活性调节价值和绿色价值不能合理体现。三是保供应的市场机制很难设立。由于电力系统不具有季节性和长周期调节能力,在季节性和长周期的保供上,仍需要政府发挥调控作用,难以建立保供的市场化机制。
源网荷储规划与投资协调的体制机制缺乏。一是电与煤的规划与投资协调不足,造成电与煤冲突问题长期存在。煤炭与煤电的产能周期矛盾导致煤电供需周期性错配;煤炭、煤电布局与产业发展逆向分布导致煤炭和煤电源荷错配;煤炭供应中周期性和季节性波动长期存在,煤炭储备对于协调煤电矛盾的调节功能不足。二是电源与电网的规划与投资不匹配,造成新能源电力接入输送问题大。电源投资与电网投资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在投资回报率考核要求下电网投资规模难以和电源投资相匹配,不利于新能源电力接入输送。三是储能建设的规划与投资不能形成长期预期,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消纳能力不足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在源网荷侧的储能建设缺乏系统的规划和投资统筹,不能在建设周期、产能与需求方面形成长期可预期的可持续机制,电源侧强制配储和利用率低同时存在,难以有效发挥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消纳能力的作用。
(三)电力系统低碳转型风险约束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电力系统低碳转型是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电力系统的低碳改造升级和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两方面,是培育形成能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但这两方面均存在技术瓶颈和经济成本过高等风险,使得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通道存在一系列“堵点”和“断点”问题。
在传统电力系统的低碳改造升级方面,主要着力于电力生产环节的低碳改造,以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为主,目前仍存在改造投资能力不足、缺乏有效回报机制,改造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还不能完全满足技术的可行性、经济性和运行安全性要求。特别在灵活性改造方面,低负荷运行时能效和发电量下降,燃料成本和度电煤耗上升,发电收益减少,在调节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改造投资发生亏损的风险较高。同时,灵活性技术仍不成熟,还存在一定的安全运行风险。
在新能源电力系统发展方面,主要着力于以光伏发电、风电等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的发展,包括源网荷储各环节及一体化发展,目前存在着技术不成熟、应用场景发展不足、“内卷式”竞争严重、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会导致新能源电力消纳水平偏低、弃风弃光率偏高、出力不稳定、安全兜底压力大、行业普遍亏损、新业态盈利模式不明确、新技术应用的收益率低、高碳锁定等系列风险。
三、高质量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对策建议
“十四五”末期乃至“十五五”时期,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进程,在“立”与“破”的协调推进中实现电力高水平安全,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有效有序推进电力系统“两化”转型发展,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培育形成能源新质生产力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在“立”与“破”协调推进中实现电力高水平安全
逐步改革能源体制机制,推动煤炭与新能源、煤电与可再生能源电力融合发展,并在技术上逐渐明确煤电和煤炭的安全兜底边界,探索“立”与“破”协调推进的路径,在新能源与新能源电力有序发展的同时,推动煤炭与煤电的安全减量替代,实现从主体到基荷再到应急备用功能的转变,真正发挥好煤炭与煤电安全兜底的战略功能,同时推动新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如在“十四五”末期至“十五五”时期,煤电作为主体电力的功能会小幅弱化,作为基荷电力发挥的调节功能会逐渐加强,电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将加快发展,将推动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取得新突破,应统筹好新能源电力消纳供给“立”、煤电主体电力功能“破”和基荷电力调节功能“立”的关系,在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可靠的基础上,实现新能源电力对煤电在主体电力功能上的替代行动。充分发挥国家能源储备体系战略功能,降低突发情境下的电力系统运行风险,提高电力系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健全电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重预防机制,深入落实电力安全风险管控行动计划,推动解决大电网风险管控、局部电网补强、电力行业网络安全以及建设施工人身事故防范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电力波动的早期预警系统、预警响应系统和处置反馈系统。重点提高灾害多发地区防灾抗灾能力,加强关键骨干电网建设,保障极端条件下核心电网安全。提高地方政府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处置协调能力,健全跨地区应急救援资源共享及联合处置机制,推进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能力示范县(市)建设。完善电力企业应急能力建设评估工作长效机制,滚动提升电力企业应急能力,做好重大活动和重要时段保电工作。继续推进国家级电力应急救援基地建设,建设电力行业应急资源信息共享平台,盘活闲置应急资源,实现应急物资的共享应用。构建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多品种能源应急供给体系,并深入推进电网调度、辅助服务等电力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提高电力系统消纳供给灵活性,提升电力系统应对突发事件风险的抗冲击能力。
(二)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制机制建设
破除新能源供给消纳、适于新型电力系统特征的电网运行、新型储能等参与市场交易和定价等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充分竞争的全国统一竞争性电力大市场,为形成绿色生产力中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奠定基础。一是破解新能源电力开发、并网、输配、消纳中存在的技术、要素、体制障碍,不断完善新能源电力供给消纳体系。如强化对大型风光基地、分布式能源、调峰电源、特高压输变线路建设的土地、环境、金融信贷、法律法规等要素保障。二是加大电网改革力度,建立增量配电网常态化发展机制,构建适应“源网荷储互动”特征,并兼具集中灵活性和分散灵活性的智能电网运行体制机制。如加强对微电网、区域性电网发展的支持。三是加快建设多层次的新能源电力市场体系,完善电力现货、辅助服务、容量、跨省跨区输电权等市场的体制机制建设。分阶段有序完善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的机制建设,通过保障性消纳、强制配额、绿证、碳市场、市场交易等机制建设,优化现货价格、中长期合约价格、参与跨省价格、联营价格等形成机制,建立适应新能源特性的市场机制;重视多年调节水电站等长周期储能建设,在完善电力系统长周期调节功能的基础上,运用市场化运营定价逐渐实现成本的可负担;加强市场与政策调控的协调机制建设,实现燃料价格、电价、用户价格联动变化挂钩机制,有效释放现货市场的信号,完善辅助服务定价、不同功能电源定价等机制建设。
建立和完善源网荷储规划与投资协调的体制机制。一是加强煤与电的规划和投资协调,逐步解决煤炭与煤电冲突问题。综合考虑煤炭和煤电产能、储备与建设周期、负荷需求,协调好煤炭与煤电的规划和投资,进一步完善煤炭储备制度建设,深入解决煤电产能周期性错配和源荷错配矛盾。二是统筹协调好电源与电网的规划与投资,形成有利于新能源电力接入输送的机制。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股份制改革等方式营造一个更为开放的电网投资环境,改革电网单一投资回报率的考核制度,加强宏观规划的统筹和源网规划的协调,使电源投资与电网投资相匹配,为新能源电力顺利接入输送奠定良好基础。三是优化源网荷各端的储能建设规划与投资,有效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消纳能力。加强源网荷储规划的协调,形成与新型能源体系特定发展阶段需求相适应的储能规划与投资建设机制,以技术成熟、经济成本可负担、利用率高的储能建设,持续增强电力系统调节和消纳能力。
(三)有效有序推进电力系统“两化”转型发展
有效有序推动电力系统绿色低碳化、数字化“两化”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加快培育形成能源电力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能源技术与绿色低碳技术、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的融合发展,大力支持电力企业与绿色低碳技术企业、数字化技术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进电力行业与绿色低碳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
在推动电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面,应疏通电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中的成本价值传导机制,让环境成本与价值通过完善的价格机制得到完全显现。加大财政、金融政策对电力系统碳减排的支持力度,通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多种措施,完善煤电“三改联动”投资回报机制,提高煤电企业改造升级的积极性。以提升终端电气化率为抓手,加快推进电能替代,并着力于CCS(碳捕获与封存)、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的深入研发和商业化应用,攻克电力系统深度脱碳难题。
在推动电力系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方面,应强化对电力系统特定场景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的支持,特别要支持新型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所需要的电力芯片、软件、智能设备装备等方面的研发创新及应用。支持电力企业牵头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所需要的产品,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企业共同研发生产。支持头部企业申报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政策平台,通过保障前沿技术或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先占收益,激励技术先进企业发挥牵引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作用。
袁惊柱.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进展、主要风险与对策建议[J].中国国情国力,2025,(02):4-8.DOI:10.13561/j.cnki.zggqgl.2025.02.002.